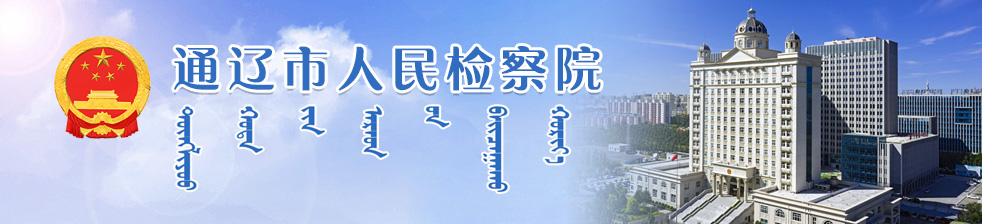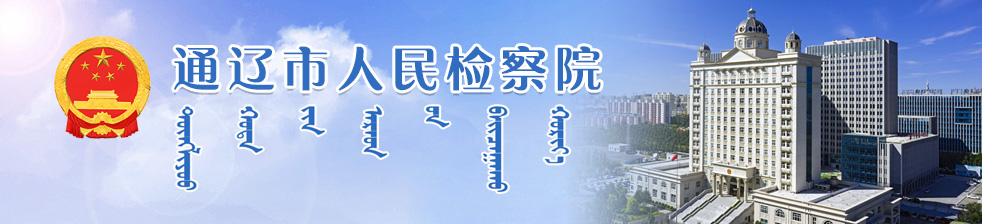该案已经超过20年追诉时效期限,刑法也经过了1979年和1997年两次修订,修订后的刑法改变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,将“采取强制措施”变更为“立案侦查”。根据现行刑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,追诉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,如果适用旧法“采取强制措施”的规定,则追诉期限已过,如果追诉,应当报请最高检核准;如果适用新法“立案侦查”的规定,司法机关可以直接追诉。
拿着厚重发黄的卷宗,我的内心无比沉重,面对新旧法变更的问题,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,真正实现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正义?

经过深入研究、梳理思路,我认为时效制度的存在,是为了督促侦查机关尽快破案,对于未能侦破的案件,通过时效制度让社会重新归于稳定。追诉制度正是时效制度的一体两面,时效制度能够消弭大部分久悬未决的案件,但是对于一些时效制度不能够解决的刑事犯罪,则可以通过核准追诉制度实现刑法上的报应。
当然,报请核准追诉条件和核准追诉必要条件都有客观和明确的标准。该案虽然发生在信息并不发达的23年前,案发时消息没有得到广泛传播,案件侦破后,也没有像某些案件一样引起舆论震动,但这一犯罪事实的恶劣性和影响性是经年不衰的,即便经过23年,任何人再次亲历当年案卷,也都会将其认定为“影响性特别严重”。
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发现,犯罪的影响性特别严重是一种客观事实上的判断,而不是一种主观上的判断。因此,我认为,无论从溯及力原则的普遍适用性还是时效制度的价值平衡性,或是核准追诉标准的客观性上看,该案都应当报请核准追诉。我的观点得到了员额检察官联席会的同意。

这是我从检10年来参与办理的唯一一起核准追诉案件,也是我院建立以来办理的第一起核准追诉案件,且成功被最高检核准。尽管该案办理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论和程序难题,但是通过难题破解并积极报请,最终使得尘封多年的命案得以报偿。死者能够安息,生者得以慰藉,犯罪人在法律程序的正义下获得应有判决,法律的双向平等保护在司法实践中、检察为民的初心在个案中不断得到体现。
案件办结后,回想此案的办理过程,我有几点感悟:一是案件办理要遵循刑法基本原则,准确认定溯及力适用范围。二是案件办理要把握时效制度原理,审慎适用核准追诉制度。三是案件办理要准确适用核准追诉的法律规定,准确把握核准追诉报请条件。报请核准追诉的条件,是一个案件能否被追诉的客观标准,这就要求办案人秉持客观公正立场,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量追诉“必要性”,严格审核证据标准。